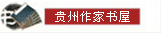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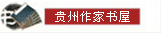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一到中午十二点钟,王子厚的擀面皮店便关门打烊了。其实,街上别的擀面皮店大多关门在中午两三点钟后。李桂兰曾在王子厚耳边嘀咕,咱早上面皮多蒸些,咱也中午两三点后关门。王子厚哼了一声,不以为然说:“钱要大家伙来挣呢,咱一家能把世上的钱挣完?!”
王子厚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
中午饭一吃罢,王子厚时常要美美睡一觉。这时候,整个县城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一丝一毫都听不见了,只有一片漆黑香甜的睡眠,只有王子厚喉咙里扯出的,一声声雷鸣似的打鼾声。用女人李桂兰的话说,这时候王子厚就是被人提起胳膊抡着腿,扔到县城背后的砚瓦沟,人都不会清醒呢。但下午三点一过,王子厚准时会醒来。洗把脸,泡一缸茶,然后拎着那把他常坐的帆布靠背椅,出门了。
每个下午,王子厚要在他擀面皮店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坐一两个小时。有时给隔壁开批发部的房东老万发支烟,扯扯闲话,大多数时候,王子厚抿几口茶,然后点支烟,望着面前来来往往的行人,眼都不眨地瞅。现在,早已打了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下午后半晌的太阳光清油样红彤彤泼在王子厚鬓角已有几根白发的头上,落在他的眼睛、眉毛、眼睑上,像盆温吞吞的热水,照得人怪舒服。这是王子厚一天里最为惬意的时候,他佯着眼,瞅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行人,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穿西服打领带的县城机关干部,衣着邋遢、落伍的上县城看病或是逛街的农村人,偶尔,有熟人迈过脸,“王师”或“老王”亲热地高呼一声,跟王子厚打个招呼。
栖凤巷是个曲曲折折约莫有一里长的老巷子,早先这里是个村庄,后来渐渐被县城的高楼大厦四面围裹住,成了个城中村。巷子里的住户,有的院前院后盖起了楼房,出租屋子当起了房东,也有的院落里,还是早先盖的砖瓦厦房,但家家户户门前,清一色都是做买卖的店铺。有王子厚的擀面皮店一般大小的小吃店,还有扯面馆、饺子馆、羊肉泡馍馆,也有批发部、调料店、水果店之类的店部,县城附近的人,平时总要挑着他们地头种的菠菜、白菜、大葱、蒜苗来栖凤巷里叫卖,因此呢,栖凤巷里虽说整天拥拥挤挤吵吵嚷嚷,却有着县城里别处没有的旺腾腾的烟火气。县城里的人,有事没事总要去栖凤巷里转转,下午后半晌,是栖凤巷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巷子的街道上,是川流不息的人流,巷边的门廊里,左一家摆着麻将牌桌,右一家是个棋摊,一个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凑在一起在下棋,在打一两块钱的小麻将,越发使得栖凤巷显得更热闹了。王子厚不打麻将,也不下棋,王子厚只喜欢瞧街上的热闹。
有时候,他会迈过头,朝东边的巷口望一阵。巷口太平路东边,太平塔像个得道的高僧,兀然矗立着,不管是春夏也好秋冬也好,也不管这座县城是喧闹也好凄清也好,就那样孤零零矗立着。太平塔是座八角九层密檐式砖塔,据说有三十多米高,房东老万常说,太平塔可是个宝物,栖凤巷这些年之所以顺风顺水,全是因了这座宝塔镇着!老万还说,太平塔自北宋元祐年间修建到现在,有九百多年呢,有塔必有寺,他在县志上看过,这里原来有座寺,叫太平寺,后来寺毁了,只独独留下这座塔。太平塔的东面,是栖凤巷和周边的孩子上学读书的学校,叫塔下小学,老万曾神神秘秘跟王子厚说,县上规划要将塔下小学搬到县城北环路去,将太平塔这一带地方腾出来,要建一个太平塔旅游景区,据说图纸都设计好了。不过,风大雨点小,至今王子厚还看不出有丝毫动静。瞅着远处的太平塔,王子厚总在心里想,这座塔陪伴过县城里多少代人啊,多少人不在了,但太平塔依旧还在!将来也一定还会在!
日头快要沉进巷子西头的楼群中,栖凤巷像被镀上了一层金粉样,笼上了夕阳红的辉光。这时候,对面满娃馍店的馒头出锅了。一缕缕白亮亮的雾气从大开的店门上飘出来,满娃和媳妇将几屉刚出锅的馒头抬出来,摆在店前搭建的遮阳棚下。王子厚抽抽鼻子,不久他就闻到了,远远飘来的刚出锅的馒头,那种热烘烘的清香味。
王子厚喜欢吃满娃馍店的馒头,下午要花一块钱,买四个刚出锅的馒头,再炒盘粉条拌洋芋丝,喝碗稀饭,他和李桂兰的晚饭就算是解决了。打馍店前经过,王子厚时常身子一扭,就进了满娃的馍店。
馍店里一年四季热烘烘的,飘着股刚出锅的馒头所散发出的白亮亮的热气和麦面馒头所独有的清香味,王子厚还喜欢嗅,那种夹杂在馒头的清香气中,一丝丝发面的酵子酸唧唧的甜味儿。满娃馍店里常蒸的,除过一块钱四个的小馒头,还蒸那种县城里的人遇着白事走亲戚要带的,比老碗还要大的“献祭”。 一屉屉“献祭”出了锅, 一个个白生生,又白又大,有些馍顶裂开一道花,简直像盛开的牡丹花一样好看,满娃和媳妇在蒸屉边挨个翻动着。满娃媳妇一瞅着王子厚,总会直起身从身边蒸屉里掰一块馍,递给王子厚:“叔,你尝尝,暄不暄?”起初一段时间,王子厚还会推让一番,后来渐渐熟了,他会嘿嘿笑着接过热乎乎的馍片,就往嘴里送。刚出锅的馒头,又软又暄,简直像团软乎乎的雪,只嚼几下,就“咕儿”一声滑进了喉咙。
满娃是个三十出头胖墩墩的小伙子,每天馍店门一开,不是在瓷盆里起面就是在案板上揉面,极少有闲着的时候。满娃话不多,碰着人嘴一咧,龇牙一笑,就算和人打了招呼。老话说一个哭的搭个笑的,可不是,馍店里常听见的,是满娃媳妇那略带东府口音的脆亮声音——
“叔,你慢走!”
“姨,今天买几个馍?”
嘴甜得像抹了蜜,对谁都仰着一张笑脸,说话时语气里有一种只有外乡来本地做生意的人,才会有的那种恭维巴结神情。
满娃和媳妇是关中东府一带人,具体哪个县王子厚记不清了,或许满娃说过,王子厚没记住,就是记住又有啥用呢,王子厚一辈子连省城都没去过,他肯定去不了那里!
满娃房东一家人在外地,好多年都没见回来过,满娃索性租下了整个院子。按满娃媳妇的说法,他们想把老家上学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接过来,一家人全住一起,省得他们老操心挂念。还说,乡下孩子野惯了,不是打就是闹,住个独门独院,省得吵扰别人。话虽这样说,但一直没见有啥动静,又说,唉!故土难离,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过几年再说吧。馍店关门的时候,馍店旁的大铁门时常紧关着,整个院子显得特别清静。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贵州站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