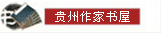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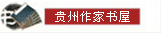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首先,正如上文所言,新诗之“新”并不单纯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它的生成和展开同步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进程中,20世纪20年代之后不断高涨的社会思潮、革命思潮也构成了强劲的激荡。这些看似外部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不仅影响了新诗的精神气质和主题取向,同时也在内部塑造了其感受力和想象力。像周作人的《小河》,曾被胡适称为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胡适的评价不仅给出了《小河》的历史定位,同时也借此传达了他的新诗理解,《小河》之所以堪称杰作是因其散文化体式带来的表达自由。针对这一经典评价,学案《周作人的〈小河〉与“新村主义”》立足原初史料,辨析了“五四”时期周作人与“新村主义”的关系,提出如果将周作人的白话诗写作理解为新诗的一个起点的话,通过这一时期思想及社会活动的梳理,恰好能说明这个起点不简单呈现在文白交替的逻辑中,而是和新村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思潮有非常内在的关联。这些思潮不仅充当着新诗的发生背景,其实也为新诗写作提供了丰沛的感性。如果说胡适的《谈新诗》从形式的角度阐发了新诗成立的“金科玉律”,那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1920年起,早期新诗理论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献,如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以及后来叶圣陶的《诗的源泉》等,的确不同程度跳脱“形式”的框架,将新诗人的人格、诗人的修养看作是新诗得以确立的关键。《早期新诗人为什么讨论“修养”问题》这一学案,也是回到“五四”之后青年群体特定的言论空间中,认为这种“向内转”的趋向,动力与其说来自新诗写作的内部,毋宁说是发生于当时青年人格、修养讨论的总体氛围之中,并由此延伸至新诗“源泉”“诗与劳动”“平民与贵族”等问题的考察。上述两个学案,都是聚焦于社会改造思潮和早期新诗写作、观念的内在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相互推动、高度同一之关系的显现。“五四”落潮之后,新诗的讨论和实践似乎逐渐从社会文化的场域中游离出来,其展开的动力也更多落回自身的形式和诗美方面。像1926年4月由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的《晨报·诗镌》,就强调形式、音节方面的“创格”实验,由此纠正早期新诗的散漫作风,开启了新诗格律化的阶段,这似乎已是一种文学史的常识。然而,《诗镌》的创办恰恰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久,创刊号上也集中发表了许多回应惨案的诗文。按照闻一多的说法,“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镌》的创立,不单是一种“碰巧”,更有诗学上的必然性。从这一特别的论述出发,本卷也专门设计了一个学案,通过梳理闻一多等人在“三一八”前后的政治参与、诗学观念和诗体实验,从另一角度揭示了新诗“创格”的意义:形式的锤炼之外,“创格”也指向了历史钢针触碰时一种特殊主体构造的生成。这也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写作的转换,并不单纯是形式“纠正”的问题,剧烈变动的历史境遇“碰巧”构成了一种内在加速、一种强力塑形。
其次,将新诗放在宽广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去重新审视,除了要关注社会思潮、历史进程内在的介入与塑造,同时也有必要考察新诗的传播、接受、社会影响,以及其和出版文化、文人群落等诸多方面的关系。要展开后一面向,某种文学社会学或文学“场域”的视角,显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卷中也纳入了相关的几个“学案”,其中有以《女神》的接受为中心展开的对“五四”之后新诗阅读状况、阅读程式的讨论,也有从出版文化与新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对于“亚东图书馆”和“泰东图书局”两家新诗“专卖店”的对照分析。《作为编辑的徐志摩》这个学案,选择一个特别的视角来审视这位“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浪漫气息的诗人”,细致梳理了他不同阶段的编辑实践,包括接编《晨报副刊》、开辟《诗镌》和《剧刊》,后又主持《新月》《诗刊》。编辑事业贯穿了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广阔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途径,在当时“自由派”知识群体的相关文化政治活动中,徐志摩可以说是一个线索性人物,用奚密教授的话来说,他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game changer”,在不同文化“场域”的穿梭中能够改变规则、创造新的可能。由此可以延伸思考的是,在现代文化转型和建构过程中,“新诗人”的位置绝非那么边缘,往往能够关联各方、起到一种凝聚和转换的作用,以新诗为媒介形成的社会连接、带动的“场域”重构,思考新诗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面向。比如,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坛十分繁盛,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等“化欧”又“化古”的努力,成绩斐然,代表了新诗发展的一个“高光”阶段。这种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当时北平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和大小文学群体的错落。《朱光潜的“读诗会”和一场诗歌论争》就以30年代在北平文化圈名闻遐迩的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为对象,在北平知识分子群体“文艺沙龙”的历史脉络中,非常细致考察了朱光潜周边文人群落的构成,其中包括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罗念生、叶公超等已成名的前辈或者学院里的师长,以及卞之琳、孙作云、董同和、张清常等北平高校的学生辈或文坛新秀。“读诗会”除作品诵读、学术演讲、论辩等活动之外,也着手杂志的创办和编辑,30年代北平诗歌界、知识界对于“新诗格律”的关切,有关新诗“难懂”问题的争论,也正生成于这样的群体氛围中。《梁宗岱与〈大公报·文艺·诗特刊〉》刚好与上一学案衔接,讨论了“读诗会”同人的诗学探讨,在报刊上的同样聚焦于“京派诗人”。《汉园聚散皆由诗》则在聚合离散的视野中,探讨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位“汉园诗人”同步又交错的文学路径。以《汉园集》这个“点”,该学案引出了几条延伸出来的“线”,讨论了不同历史脉络如何走向这个“点”,又从这个“点”再出发走向新的方向,呈现了“京派诗人”在历史中动态展开的可能性。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贵州站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