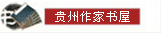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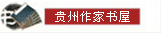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1931年,梁实秋谈及新文学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曾有一个著名的判断:“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这个说法或许有些极端,但新诗的生成和展开,确实离不开外来诗歌、文学翻译实践的多方面影响。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就自我指认,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就是一首翻译的诗歌《关不住了》,作者是美国女诗人萨拉·蒂斯黛尔。围绕此“事”完成的学案,不仅详细比较了此诗不同的译本,揭示出胡适翻译在“质”与“形”两方面的突破,又回溯晚清以来的学术和文学翻译,从“新诗现代性”和“翻译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整体讨论了诗歌翻译如何为新诗带来新的诗体、语感、新的“国家”意识和“人”的观念。如果开放讨论的视野,外来资源的影响并不限于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其牵连的话题领域十分广阔,既有内部的形式和诗学变革,也有外部的人和事的汇合、变动。本卷之中两个重头“学案”,尤其值得重视。1924年泰戈尔访华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轰动一时,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泰戈尔访华与新月社》这一学案,收集了当时报刊上的大量资料,相当细腻地描述了徐志摩等人为了迎接泰戈尔访华,组织人马排演泰氏《齐德拉》的过程。这次公演有其特定的文化象征性,吸引了众多文化名流的积极参与,更有意味的是,我们熟悉的新月社正是因为这次公演,才由较为松散的“聚餐会”向正式的社团过渡。由此,也有了后来《晨报·诗镌》《晨报·剧刊》的创办。除了挖掘泰戈尔访华事件的前后过程和丰富细节,该学案也提醒我们注意,像新月社这样的文人群落实际展开了多种路径的文化实践,新诗的格律化探索与他们发起的国剧运动的内在联系及背后的文化诉求,很值得进一步探问。相比于泰戈尔访华,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新批评”学派的理论巨擘瑞恰慈的多次访华经历,似乎不太为人关注,但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瑞恰慈在中国的讲学和多位学者的交往,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传统的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让“新批评”的学说、方法和基本理念融入了新诗理论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中。有关瑞恰慈访华的过程及影响,以往也有相关的评述和研究,但并不十分深入,本卷收入的《瑞恰慈在现代中国的交游、事迹及其著述的译介和反响》采用史料钩沉、整理的方法,极为全面、翔实地梳理瑞恰慈在现代中国的交游、授课、演讲以及《科学与诗》等著述的译介和反响,文章功力深厚,在材料方面也竭泽而渔。与瑞恰慈有所关联的学者人数众多,上一学案涉及有黄子通、李安宅、吴世昌、郭本道、叶公超、朱自清、水天同、陈西滢、费鉴照、张沅长、温源宁、邢光祖、钱锺书、朱光潜、袁可嘉等。像朱自清,就有意识运用瑞恰慈的核心观点与重要术语来重新审视中国诗学传统,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另一学案的主角青年诗人曹葆华,恰好也是瑞恰慈的重要译者,他选修过瑞恰慈在清华开设的课程,翻译了《现代诗论》和《科学与诗》两本重要的诗论集,汇集了瑞恰慈、艾略特、瓦雷里等人的代表性诗论,并且在主编《北平晨报》附刊《诗与批评》期间,译介西方现代诗论,聚合当时北平的学院诗人。正是在与西方现代诗学资源的对话中,一代新的“前线诗人”由此成长起来。上述几个学案,都涉及外国诗人和诗学的影响,但都并非一般的影响研究,而是立足于更开阔的学术文化视野,将校园环境、学术氛围、城市文化空间以及报刊传媒等因素综合纳入考察之中。
上述三个方面,或许更多指向新诗与外部的关联,更多着力于“打通周边”,这并非意味着新诗形式、美学问题遗落在“学案”的视野之外。正如前面谈到的,一些特定时刻、特定个体的写作和诗学实践,有可能因被纳入线性的新诗演进叙述,而被“抹平”其内在的褶皱、差异和独特性。因此,一些看似已有定论的新诗个案,其实很有必要重新审视。本卷第一个“学案”,就重新检讨了胡适“白话诗”主张提出过程中的一次“偶然”、一次由“小船的打翻”引发的胡适与友人之间围绕具体作品修改展开的争论。在胡适的自述中,这次“偶然”被比较流畅地组织到白话诗觉悟形成的过程中,但如果回到争论的前后过程,可以发现胡适最初“诗国革命”的方案中包含了“文与质”“诗与文”“文与白”的多重张力,“救文胜之弊”是他思考的起点,这与新文化“修辞立诚”的初衷紧密相关。后来,胡适的思考收缩到语言形式的层面,原有方案的弹性空间以及伦理意涵,反而有可能隐而不彰。呈现新诗展开多重层次、内在张力的努力,可能也隐含于后面的学案中。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废名和林庚围绕新诗与旧诗、自由诗与格律诗的讨论已为人熟知,往往也会被放入当时“格律”和“自由”两派不同的立场中去理解。但如果进入废名、林庚各自的论述脉络中,会发现其实他们都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胡适确立的工具论新诗观和线性的新诗演进逻辑,更多从诗歌内在的表达机制层面,以古典文学为认识和论述的资源,在共时性的文学视野中去探讨新诗成立的前提和自我改善的路径。像林庚讨论“自由诗”和“格律诗”(“韵律诗”)区别,就不只着眼诗歌的形式层面,而是从“文”和“质”的关系入手,去把握新诗的内在气质和文化风格:自由诗的“紧张惊警”代表了新诗冲破审美惯习的先锋活力,而“格律诗”又被他命名为“自然诗”,其“从容自然”的气质,意味了新诗走出偏执的个体感受,走向某种公共性的可能。这些讨论的意义,显然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自由与格律之辩,而是包含了对新诗的整体性反思,对思考新诗的当代前景也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在30年代,与北方“前线诗人”遥相呼应的,是上海的“现代派”诗人。其中,戴望舒的《雨巷》是新诗史上的名作,似乎完美体现了古典诗词美感、意境在新诗中的延续,关于这首诗的阐释也十分充分,按道理,不应该成为一个“学案”。《〈雨巷〉与“新感觉派”》却选取了一个“诗”与“小说”联动的视角,将《雨巷》与“新感觉派”的小说(刘呐鸥的《热情之骨》、穆时英的《夜》、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对读,联系几位作者日常密切的交往,讨论了小说对诗的袭用和模仿,揭示了现代性感受和欲望机制在不同文体之间的流动。这个“学案”以小见大,从单一作品的重读入手,更换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时性阐释,横向拉出了一个共时的、跨文体的维度。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贵州站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