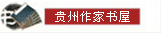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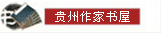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最后,还有一个可以注意的面向,那就是相对于新文学其他文体,新诗大概是最擅长“戏台里叫好”的,新诗的展开也一直伴随着自身形象的塑造、生产。这种形象生产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达成,如诗集的编撰、由序言和批评完成的“包装”、诗歌选本的编定、经典作品的选择以及新诗自身历史的讲述等。本卷也有几个“学案”,尝试从这个方面展开讨论。像《早期新诗“选本”中的“分类法”和“读者眼光”》,系统考察了1920—1922年间出现的四种新诗选本,在分析不同编选策略和作品来源的基础上,探讨了作品分类方式转换中新诗观念的生成,又以不同编者撰写的评语、导读为线索,透视出早期新诗“阅读程式”的建立。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新诗选本,自然非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莫属。《朱自清的新诗“中衰”说》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注意到了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一个说法:1924年小诗运动偃旗息鼓到1926年《晨报·诗镌》发行的这段时间,被他称为中国新诗的“中衰期”。从这个特别的说法入手,该学案延伸开去,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多种新诗史“分期说”,并回到1924—1925年的新诗创作、阅读语境,澄清了“中衰期”的具体含义,并以此作为思考20年代新诗内在危机和转机的特殊视角。确实,30年代有关早期新诗“分期”的讨论非常多见,许多批评家都试图采用“三阶段”“前后两期”等方式整体鸟瞰新诗的历史。这与30年代新诗站稳脚跟之后的自我叙述冲动相关,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是,新诗在30年代开始进入大学课堂,成为系统研究、讲述的对象。早期新诗的线索复杂、备受争议,只有梳理出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这段历史才能从不确定的、实验的氛围中落实下来,成为一种可以把握的“知识”,“分期”讨论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本卷最后一个学案,就以30年代朱自清、沈从文、苏雪林、废名等人的新诗史讲义为对象,分析了这些讲义背后不同的逻辑和动机。考虑到包括“分期”讨论在内的30年代新诗史讲述,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以线性演进为中心的新诗史观。怎么突破线性的、知识化的新诗史叙述,在特定问题意识和现实关联中开放新诗研究的空间,正是“学案”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以该学案作为整卷的收束,似乎有了某种“卒章显志”的意味。
以上五个方面,不能完全概括第一卷“学案”的全部,但大致能标识用心之所在。当然,这30个“学案”还只是一些特别的“点”,并不能涵盖早期新诗的全部问题。比如,大革命前后兴起的左翼革命诗歌,在“五四”之后从“自由”到“格律”的脉络之外,其实构成了另一种新诗的传统,不仅强化了新诗与20世纪历史的关联,同时也突破了印刷媒介的限制和知识分子读者的圈层,让新诗可以朝向行动、朝向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动员敞开。涉及此这一脉络的“学案”目前只有三个,原来计划中的一些构想,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及完成,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另外,已有的“学案”也可能存在散漫、布局不均衡、风格不太统一、“论”多于“事”等问题。这些遗憾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来弥补了。换个角度看,这或许也说明了“百年学案”工作的开启性、可能性:从“历史的兴趣”出发,关注新诗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重联系,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固化的线性叙述,展示更多的丰富性,同时也是在为将来全新的、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感的新诗史写作,提供材料、方法的积累和准备。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贵州站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