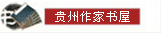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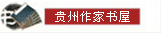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再回来看《一蓑烟雨》,我觉得就更容易理解了,与《时间笔记》相比,它并未显现什么转折,而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不过气息和气象更加笃定,更气定神闲——“定风波”的含义可能就在这里。“一蓑烟雨”的自我想象,是一种自愿自得和悠然自适,而不是自怨自艾的自我悲叹,是“愿意,就这么任性”。是无所谓风雨和阴晴,对自己来说都一样的境遇,“卿可奈何”?
这当然便应该是60岁以后的境界了。想必当年东坡先生还远不及这个年纪,就已经悟出此境,但毕竟今人比古人活得更长,自然也不宜太早,太早则有造作之嫌。这是我从梁平兄诗中所感悟到的一点对我来说尤为重要的东西。
看一下诗集末尾的“自言自语或几个备注”,会留意到诗人所提醒的几个关键词。将之串起来看,基本上也可以明了其大旨了。“躲进小楼”,首先是一种态度,就是尽量保持自我的独立,即“内心的宁静”,惟有删繁就简的生活,方能净化周边和净化自我,以此来强化“我”的力量,这是第二个关键词,也即“主体”。风波能定,全凭“我”之定力,这个定力哪里来,当然是来自生命的彻悟,悟则无惧,犹无欲则刚,由此可自如地进入他的世界,且有游刃有余的自得与自信。
接下来是他的“根”“历史”“现实”,还有“叙事”的“备注”。这些我想是说他的诗歌疆域,是包括了由“根”所隐喻的“文化”——对地域、地方文化以及在此根基上所展开的生存状态的梳理与认知;还有就是“历史”和“现实”的感受与介入,这一点我想不必多说,是表明他对诗境与诗意之纵深感与现实感的两种诉求,或者说,是出于建立他的诗歌之“宽度”与“深度”以及“系统性”的需求。这从他诗集中大量刻意保有的“组诗”“系列诗”的痕迹中,都可以看得出。至于“叙事”,则是他对于自己在文体与写作风格方面的一个自我彰显和阐释。
如其所述,我在这本《一蓑烟雨》中读到了他对古今众多诗人的凭吊之作,其中涉及屈子、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还有扬雄、李白、杜甫,有韦庄和清照等等,这些都属精神或诗的对话,或者也可以说,是梁平穿上了各个时代的衣裳,化作古人在说话;再者是各处作为文化标识的地域,从成都的草堂,到蜀地的蜀道、阆中、剑门关,到更远方的东湖、衡山、闽南,到良渚、西双版纳、哈尔滨,还有更遥远的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每到一处,他必然吟咏这里的自然、历史与文化,托物言志,述景寄情,这些我必须说,都写得干练、老辣、时有警句,还有一种删繁就简“速读般掠过”的气势。即便是写到“苏小小”“董小宛”“柳如是”的几篇,也舍不得稍加盘桓,有些许缠绵。我想,也许这便是梁平了,他见得太多,走得太远,没法不快。古人言“少不入蜀,老不出川”,川地的优游自乐,让一切他乡的美景良辰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就像韦庄《思归》诗里所说,“外地见花终寂寞,异乡闻乐更凄凉。”我们的梁老大归根结底不是个喜欢哀伤和凄婉的主儿,而是一个杀伐果决举重若轻的侠客。所以,他总是用不怎么“正眼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纸上的古人,或是坟墓中的传奇。
但我必须说,我还是十分地喜欢《韦庄在成都》这样的诗,它是如此精短,而所含的意绪又是这般深远。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自画像”式的作品,这位韦庄一生在蜀地的荣辱浮沉,在这里的花间缠绵,那可追义山的才情,确乎令人有万千感喟。但这首诗又以逸待劳,寥寥几句就将这些可能的意绪尽行收纳。“浣花溪的晚唐和前蜀,/在一只秋蝉的号角里,落叶纷纷,/韦庄前脚与后脚沾满的泥土,比印泥鲜艳。/秦妇的感旧伤时,让说客身份反转,/宰相寻见的草堂芜没已久,欲哭/在杜工部曾经的栖身地/重结茅草为一庐。//杜甫采诗而去,茅屋为秋风破了又破/韦庄在浣花溪花间走笔,一个金句/留给了草堂”。恰似一个简版的“韦庄传”,让你遥想此人的一生,并不禁生出诸般指向作者的类比和推想。
再就是日常的“物感”与“心迹”的记录了,我喜欢梁平的这类诗。随所见所闻,写所感所念,真个是信手拈来,“吾手写吾口”,最让人会意会心。如《癸卯新年帖》,写虎年与兔年的交接,看似云淡风轻,实则有暴风骤雨之意,这个年乃是疫情后的第一个新春,每个人都似有万千思绪、百感交集。而梁平故意用一番戏谑的话语,来隐含这些感慨,反而令人心有戚戚。确乎,“老虎和兔子的交接仪式,没有一支笔可以完成记录”,这里的内心狂想与惊魂甫定,确乎难以言喻。但好在人间生活已经回来,“烟火升起,锅碗瓢盆磕碰的民谣,已是天籁,形势一片大好”。这首诗让人读之不免有带泪的笑,或是带笑的哭。这便是老梁平的笔力了。有没有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那悲喜交加的味道?“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和平和常态的生活看似平庸,却失之久矣,如今终于失而复得,犹收复大好河山一般,怎能不叫人涕泪纵横。只是像老杜一样,梁平不止克制了其中的欢喜,还压抑了表达的语言,这一点甚至有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意思了。居草堂久矣,焉能不得其味?
由此我忽想到,虽说这本诗集名之曰“一蓑烟雨”,而未称其为“草堂集”之类,像是要刻意自比东坡,但实则其中还有一个老杜,东坡是其“魂”,老杜却是其“心”;抑或换一个比喻,东坡乃其是“身”,而老杜则是其“魂”,亦未尝不可也。
这样我们也便可以找到这部《一蓑烟雨》的正解了。我以为,如果梁平的这部诗集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和价值的话,那么也应在这里。所谓境界、胸襟、气象、情志,不过如是,几千年来中国诗歌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其最高境界不过如是矣。儒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还有“儒释道三界合一”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正是选定了杜甫和苏轼这两个模本。而在梁平的诗歌背后,我分明看到了两个难以分解的样本的结合。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贵州站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