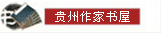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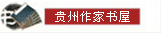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粮食问题》中的忧思,“粮食从土地魔幻到餐桌上,整个过程/罗列人类最神圣的宝典,不能穷尽/所以不敢轻描淡写”,“记住袁隆平被深耕过的脸,沟壑交错/每一道刻痕都是粮食的形状/整个世界都可以包围”。平心而论,这题目相当难以处置,他也确乎不得不用了理性的笔法,虽不讨巧,但这首诗背后,对中国人来说犹如千斤之重的民生命题却得以凸显。在另一首《旧时光》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对于历史的沉浸的思考,而且其中他擅长的诙谐笔致也得以显露,“末代皇帝剪了辫子/透过墨镜读白话写成的诗”;“金銮殿上的人死了/紫禁城一长串真名实姓/和长城正在风化的石头较劲/后海一支斑竹削成的笔/滴落泪千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沧海桑田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作者那洞烛幽微和参透真相的目光。
其实类似触动人心弦更深的作品还有很多,只是不必,或没有办法一一细解。在《等一只靴子落地》和《眼睛里的水》中,可以更直接地看到某些忧愤,“等一只靴子落地/不关心尺码,不在乎落地磕碰的声响/风也过了,雨也过了,庙堂与江湖/一张纸,不能覆盖浩荡的身体,血在燃烧”,这只将落未落的“靴子”是什么,自有特定所指,但这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会从中读出会心的焦灼。“语义学的抽屉,堆满发黄的卷纸/随便抽出一张都可以写诗。草木生烟”,历史也给诗人提供了契机,让他那满怀的忧思,成为诗意生发的源泉和动力。接下来,他甚至把这首本来“事出有因”的诗,直接变成了“述志抒怀”的诗。“天上的云彩散了,袖口的风/挽留深秋的淡酒,一杯向远,一杯向空/挂杯的晶莹甄别抒情的度数/昨夜梦见陶渊明,布衣呼应山水”,他居然从中生出了出世与归返的情怀。看似平静的意绪中,实则有雷霆蕴藏,表面平淡的修辞之中,实有风云舒卷。
大约这就是所谓“老杜的心”罢。然而还有一个“东坡的魂”呢,这个魂无处不在,反而不好解,在我看来,所谓东坡身或者魂,其实就是这么几个词:洞悉,旷达,适性,自在,而已。如果非要权威的描述,那就是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的序言中所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
这几乎是天地间的完人了。“道德家”“士大夫”这是儒家,“修炼家”和“酒仙”是道家,“心肠慈悲”“佛教徒”是释家,除此还有耶稣式的智慧,还能做“皇帝的秘书”,月光下的漫步者……这不是百科全书或人间至圣是什么。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说法凝聚起来,无非是仁者与智者的合一。林语堂说了,这样的人在人间是不会常有的,所以我们恐怕也不能把梁平说成是东坡再世,这种话也过于肉麻。但我可以说,一个诗人能够理解并且追慕这样的人格境界,能够体察并且效仿这般人生态度,也足以称得上是至高和至真之境了。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梁平,他诗中的通达与开朗,适性与自在了。你要问我,哪些作品是代表,最集中地体现着这些特点?那么我只能说,全部,他的全部作品所追求的风格与气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是为了展现这样的处境自设与生命态度,那就是——“分明是一蓑烟雨”,但他“却无惧风雨阴晴”,这就是老梁,是他的人与诗的魂魄与精神气质。
本来还想说说他自己也记挂的“叙事”问题,恐已无必要了。其实叙事也许不是多么独异的问题,但有一点,即“梁平式的语体”确乎是一个个性化的案例。他的快节奏、“轻修辞”、以逸待劳的诙谐,有时还显得有点调皮的唠叨,或是欲言又止的精略简短,与快速收束,都是通过他带有叙事意味的语势完成的。另外还有一点,即“叙事”是为了避免过于显怀的“抒情”,因为对于中年以后的写作而言,抒情是陷阱和险境重重的,弄得不好会显得酸腐或轻飘。以叙事性的语感为基调,对于“经验”的传达而言,或许更为恰切,如同老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样,其悲切之情,须掩藏于具象的叙述之中。
我还注意到,梁平的诗中总有一种非常“年轻的语感”,这其实与其叙述性笔法也有密切关系。不老,不刻意顿挫沉郁,而总有豁达的情愫与适性的意绪,这应该就是东坡之魂的作用了。如果仅是论风格,那么也可以说,他是“离东坡稍近,离老杜略远”。我想说,这种年轻的语态,与其内在的饱经沧桑之间,形成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这种语体我觉得不妨可称之为——“梁平体”。
末了我想起陆机在《文赋》中的句子,“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大体可以用来形容《一蓑烟雨》。这是一部玄览万物、细思人生、纷纭挥霍、纵横捭阖的诗集,也是一部从心所欲、万象靡集的诗集,更是一部明心见性,见其心境、心绪与心胸的诗集。梁平也因之创造了一个既有老杜之心、又有东坡之境的,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年写作”的案例。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贵州站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