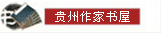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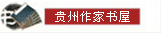
人是否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呢?或者说,人在什么时候会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命运,多么宏大又虚无的词汇,好像与此刻并无关系,无数的此刻消逝之后,它便如陆地板块般从水中突起,耸立在你的面前。
1
春节后还没出元宵,新单位就催着我去报到,当时原单位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收拾,日积月累,已蔚为壮观。过年独自回娘家的妻子,仍在假期,也还没回南宁,我便不想那么早过去。回到广西,我去编辑部交接工作,收拾办公室,一边想着等妻子回来,见一面再动身。毕竟她为了我离开家乡,留她一个人回异乡这个空荡荡的家,实在于心不忍。
这样的心绪,又不好向新单位的领导说起,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没想到他们催得那么紧,订好机票,妻子回来的第二天,简单道别,我就匆匆忙忙来到了南昌。
这并非我首次来这里。大学临近毕业时,我参加学院的暑期社会实践,一行人途经南昌站转车去延安,换乘的间隙,大家在站内的人行过道里停留了一两个小时,没有出站。那时的我困在地下通道,看着人来人往,对南昌一无所知,只知道二伯一家住在这个城市。很早以前,他们会和大伯两家人隔两年回老家一趟。那时奶奶还在世。奶奶走后,连接的纽带似乎就断了,又因年岁和病痛的缘故,渐渐地他们再未回来,而我也从未去过他们家。
研究生毕业,我通过江西出版集团招聘,来到南昌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工作。公司在红谷滩新区,与现在的新单位隔着一条赣江,中间由八一大桥相连接,桥两边分别立着黑猫白猫两座雕塑,桥的东边是滕王阁景区,距桥的西岸不远,据说是亚洲最大的摩天轮。我当时的足迹几乎都在江的西边,那个兴起不久的城区。尽管我最终去了江东边的二伯父家做客,也时常会独自一人,逛老师大旁边的书店,并且无数次去南昌站坐车回家,只是如今那些地方已是另一番模样,所以我对这个城市依然陌生。那时总觉得心里有些别的什么在怂恿着我,快走吧,不要停下来,因而当时并未觉得,自己与它建立了多么亲密的关系。一年半后,我到南宁工作,离开这里,在南宁一待便将近八年。想想,人生有多少个八年呢。
我不知道时间如何流逝。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光如水悄然而逝,如果没有和妻子走到一起,我想我会在南宁度过这辈子。回到广西,源于我对那里气候的迷恋:阳光,潮湿,漫长的夏季。这些都来自三年研究生时光,从最初抗拒,到慢慢接受、渐渐喜欢和留恋,离开时让我对这个边地省份的感受完全改观。或许那片土地就是那样子,生活之后,某种东西便会如藤蔓植物般在心底扎下根来,便不太想离开了。悠然的夏日,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绿色,近海,于我而言倾心无比。我在爸妈的支持下,在那里买了一套房子,面积不大,但旁边就有一江碧水,满足了我对简单和理想生活的渴求。每天的生活就像读书时的三点一线:家、单位、江边,与之相应就是生活、工作、运动和放松,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这几个地方消耗了。无边的生机,绿色的凝滞,让我也对时间和生命的恒久产生了幻觉,仿佛只要身在其中,自己也将融入某种永恒。
曾以为,我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但那样子的剧情,似乎是某种既定的命运,就像剧本,已被很多人完成。属于我们的命运,虽不独一,也总会被某个未知忽然改变,无论它预示着美好,还是苦难。这是否是对命运的感知呢,我不知道。忽然的转折免不了惊诧,而后欣喜,像命运突然的恩典:知晓你陷入生活的迷障,它会适时伸出手。
2
想到当时离开南昌,也是因为它的气候,只有切身感受过寒冷的人,才知道阳光的温暖。这些决定似乎无不反衬出,我是一个多么感性和不成熟的人,跟随身体最本真的感受,而不是经由大脑的思考抉择。可是二十多岁、性格内向、未曾经历多少深刻事物的人,能够思考出什么来呢?
南昌的气候,真的一时半会无法适应、接受。简单来说就是夏天热、冬天冷。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只是南昌遇到寒冷天气时,不知道从哪儿会忽然刮来大风,胡乱吹拂,几乎能把人撕得粉碎。去年在网上偶然看见一则新闻,说就是这样的风,将这里某个小区一户人家的玻璃幕墙吹走了,把住在房中的人也从睡梦中卷了出去,从高空抛落,想来多么震惊和恐怖。这种气候,就是我最初来到这个地方工作时,最直观的感受。那时工资低,伙食差,住的虽然是新楼房(宿舍),但屋里什么也没有。空调、热水器简直是奢望,只能各自想办法,有一段时间,我在屋子里热完身,然后钻入浴室洗冷水澡,而外面满是风雪。同期来到出版社的同事、室友,后来的朋友苏伟,和我一同走过了那些时刻,我们一起上下班,冬天佝偻着身体向风雪里钻,将苦涩化为玩笑调侃,在斜风冷雨中前行,才没有因此怀疑人生和命运。
似乎多少都要怀疑吧。世上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留,况且,还有曾留恋的南方城市的对比,偏偏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总需要一个说得过去、能让自己信服的理由。或许这也并非真正的原因,不然,为何在那里度过第二个冬天后,我会毅然离开呢。那时一起进入文艺社的同事,后来都在慢慢离散,我也只是其中之一,最后苏伟也离开那里,回到了北方的老家工作,慢慢安定下来。不论主动或被动,我们都听从了内心最真切的呼唤。
现在想来,在哪儿都是为了讨生活,只是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刚好出现在南昌。只有这个理由。在南宁八年,也是同一个缘故——为了活着。只是那里的环境更令我放松,让我不知不觉停留了那么久。其实那里的工资很低,假如不尝试写作,依靠些许稿费和补贴的收入,可能用不了很久,我就会因仅仅为了活着而挣扎,而忍受不了。我想,人就是在这样或实或虚的感受中,不断说服自己,不断与自己妥协,才让属于自己的日子,一点点延续下来,逐渐获得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贵州站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